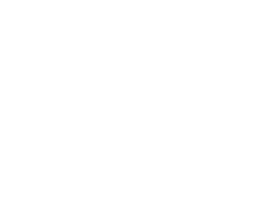- A+
索瑟姆表示,正因为考虑到这种“恐惧与无知”,他才没有告知病人给他们注射的是癌细胞,因为这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。照他的话说:“把这个可怕的词和临床实验联系起来,会对病人造成伤害,因为病人可能觉得(有可能对,也可能不对)自己要么得了癌症,要么已经无药可救……这种医学上无关紧要的小细节可能给病人情绪造成很大的影响,隐瞒这种细节……是负责任而且符合医学传统的。”
然而,索瑟姆不是这些病人的医生,他隐瞒的也不是病人的病情。欺骗病人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——要是病人知道医生给自己注射的是什么,很可能拒绝参与实验。1963年7月5日索瑟姆同布鲁克林犹太人慢性病医院的医学系主任伊曼纽尔·曼德尔(Emanuel Mandel)签订协议,要用其医院病人做实验。要不是这次合作导致事情败露,索瑟姆的实验还指不定会继续多少年。
索瑟姆打算让曼德尔手下的医生给22位病人注射癌细胞。曼德尔把计划告诉手下,并禁止他们向病人透露注射的是什么,三位年轻的犹太医生拒绝遵命,说他们不会在病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做这种实验。这三位医生都知道纳粹在犹太犯人身上做的实验,也都听说过纽伦堡审判。
16年前,也就是1947年8月20日,美国主持的纽伦堡国际战争法庭对七名纳粹医生进行宣判,判处他们绞刑。罪名是:在未经参与人同意的情况下用犹太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,比如把兄弟姐妹缝合成连体婴,为研究器官功能进行活体解剖,等等。
法庭立下十条道德准则来约束全世界的人体实验,也就是日后我们所知的《纽伦堡公约》(Nuremberg Code)。公约第一句便是:受试者必须在未受胁迫下自愿同意。这个概念是前所未有的。写于公元前4世纪的《希波克拉底誓言》(Hippocratic Oath)中并没有病人知情同意这一项。而且,虽然美国医学学会早在1910年就制定了保护实验动物的条例,但在纽伦堡公约之前竟然没有任何相关法律保护人的利益。
尽管如此,《纽伦堡公约》毕竟只是“公约”,同后来出现的许多公约一样,它们并不是法律,最多只能算是建议。医学院里未必教,包括索瑟姆在内的许多科研人员号称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。那些听说过《纽伦堡公约》的人,很多以为它是“纳粹公约”,是为野蛮人和独裁者制定的公约,和有良的美国医生没关系。
索瑟姆给病人注射海拉细胞的时间是1954年,当时美国还没有正式的研究监管机构。其实20世纪初就有政治家尝试把监管条例写入州法和联邦法,但每次都遭到医生和科研人员的抗议。因此,以“阻碍科学进展”为由,这类提案一次次遭到否决。然而在其他国家,早在1891年就有规范人体实验的条款,讽刺的是,在这些国家中,就有德国的前身普鲁士。
唯一能在美国强制推行科研伦理的办法就是通过民事法庭。律师在法庭上可以用《纽伦堡公约》来评判科学家是否符合职业道德。但想把科学家推上法庭并非易事,得有钱、有办法,并且需要知道自己被用于科研实验了。
塔斯基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查海拉细胞。
“知情同意”(informed consent)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57年的一份民事裁决中。原告是一个名叫马丁·萨尔戈(Martin Salgo)的病人。医生给他施行麻醉,他以为医生要给他做的是一项常规手术,谁知道当自己从麻醉中醒来,竟发现腰部以下已完全瘫痪。医生从没告诉他整个操作过程的风险。法官裁定医生败诉:“医生如果隐瞒必要信息,致使病人无法对即将进行的医疗做出理性判断,那他就没有履行对病人应尽的职责,是有过错的。”他还写道:“医生必须提供足够的信息,这是知情同意的基础。”
“知情同意”强调了医生必须把相关信息告知病人,但是对类似于索瑟姆的研究却没有任何约束,因为索瑟姆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他的病人。得再过几十年,人们才开始质疑,像海瑞塔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有“知情同意”的问题,这次医生是从海瑞塔体内取组织,然后在体外进行实验。
但是对那三位拒不配合索瑟姆的医生来说,未经病人同意便往他们体内注射癌细胞,是绝对违背人权的,也违反了《纽伦堡公约》。曼德尔却不是这么看的。他要一名住院医生代替这三个人给病人注射。1963年8月27日,三名医生集体辞职,辞职信中给出的理由是“违背伦理的科学研究”。他们把信交给曼德尔和至少一名记者。曼德尔收到信,立即把三位医生中的一位叫来,指责他们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背景而过分敏感。
- 我的微信
- 这是我的微信扫一扫
-

- 福利特权微信公众号
- 我的微信公众号扫一扫
-